1
我现在是老了。但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次经历,让我印象很深。我去参加剑桥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的讲座。一个非常老的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门来,举步维艰。当时我就忍不住想,他为什么要那样走路呢?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走路呢?我立刻纠正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他这样做是身不由己,我告诉自己。他太老了。
年轻时的我对一个老人的那种即时反应,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更早时候)处于正常年龄段的健康人看到老年人时心中激起的那种反应。他们知道,即便是身体算得上健康的老年人,也没办法像其他年龄组(儿童除外)的人那样正常走路。他们知道这一点,但这只是一种遥远的、并不切身的感受。他们无法想象那样一种局面,即他们自己的双腿或躯干无法正常遵循他们的意志。
我在这里故意使用了“正常”这个词。那些在年老时经历身体变化的人经常会被人不自觉地视为对社会规范的偏离。其他可以被归入正常年龄组的人经常不具备那种共情能力,不能对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的经历感同身受——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相对年轻的人来说,他们自身的经历无法支撑他们去想象,当自己的肌肉逐渐变得僵硬,身体变得肥胖臃肿,结缔组织增生,细胞生长更新也变得缓慢是怎样一种感觉。在科学领域,这种生理过程是人所共知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深刻的理解。这样主题的文学也不少。但在这些文学里,很少提到也鲜少去理解衰老的体验本身。这个话题相对而言较少被讨论。那些还没有上年纪(或者说暂时没有年老)的人如何对待长者,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给予老年人何种医疗救助,而是要更深刻地理解衰老过程中的诸多体验,同样也要更深刻地理解死亡。但是,正如我之前已经论述的,这其中很明显存在很多共情的障碍。去想象自身如此新鲜、如此惬意自足的躯体会变得迟钝、疲惫而臃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个人可能无法想象这一点,从根本上也不愿意如此。换句话说,要认同老年人和临终者,对其他年龄组的人而言有其特殊的难度。无论有意识与否,人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想自己会老,会死。
这种抵抗和压抑(我之后会回来论述这其中的原因)在发达社会中可能比欠发达社会明显得多。现在我也已到耄耋之年,我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青年人和中年人)要理解老年人身处的境况和体验是何等困难。我的很多朋友、熟人会对我说一些善意的话,比如,“天啊!你是如何保养得这么健康的?根本不像你的年纪!”或“你还在游泳?太惊人了!”。人们会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走钢丝的表演者,深知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风险,他同样也很清楚自己会抵达钢丝另一端的梯子,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悄悄回到地面。但是那些在下方仰视他的人们知道他随时有可能从空中坠落,他们紧张地、略带恐惧地看着他。
我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次经历,可以用来说明年轻人对老年人是如何缺乏同理心。当时我去德国的一所大学拜访一位教授,被他的一位风华正茂的同事邀请赴宴。宴会开始前有一道开胃酒,他邀请我坐到一张非常低矮的充满现代感的帆布椅上。他的妻子招呼我们聚到餐桌边。我站起来。他非常惊讶地甚至可能带点失望地看着我。“好吧,你身体还很棒,”他说,“不久之前我们邀请老普莱斯纳(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 1892—1985],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20世纪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出身背景和人生经历与埃利亚斯有相似之处。——译者注)来用餐。他和你一样坐在那把矮椅子上,但他没法站起来,试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我们不得不扶他站起来。”他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哈!他再也没法自己站起来!”这个主人笑得浑身发颤。很明显,在这个故事里,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恐怕很难产生共情。
那种感觉(“也许有一天我自己也会老去”)有可能是完全缺失的。剩下的只有那种完全无意识地对自身优越感的沾沾自喜,还有年轻人相较于年长者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对无助的老人的嘲讽和揶揄,对丑陋的老年男性和女性的反感厌恶,这其中所包含的那种残酷,现在也许要比过去轻一些,但从未消失。这和人们年老时或临终之际,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发生的标志性转变密切相关:当他们年纪渐长,他们在年轻人面前有可能,或者事实上将变得越来越弱小。他们对别人的依赖变得愈加明显。人们在步入老年时,如何与自己益愈加深的对他人的依赖,以及自身力量的消亡共处,其结果因人而异。整体上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自身的人格结构。如果我们记得老年人的一些行为,尤其是一些怪异的举动,和他们对自身丧失力量以及对依赖的恐惧,尤其是害怕自己失去自控力的恐惧密切相关,这一点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针对这种情况,有一种适应方式就是复归婴幼儿行为模式。我无法确定,这种婴幼儿行为模式在老年人身上的重现,仅仅是机体退化的症状,还是他们在面对一种与日俱增的脆弱性时无意识地逃离,从而复制童年早期行为模式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这同样代表了一种对完全依赖性情境的适应,这种依赖性有其内在的痛苦,但同样也有带来满足感的部分。事实是,在很多老年人的家里,很多人需要像小孩子那样被人喂食,需要有人为他们拿好便壶,需要有人帮他们洗澡清理。他们同样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对权力进行抗辩和斗争。一个对他们稍微有点苛责的夜班护士可能整晚都会被每小时响一次的闹铃吵醒。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它们说明我们很难理解老年人的经历,除非我们意识到,衰老总是会让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让他与其他人的整个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一个人到六七十岁,或者八九十岁时,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或快或慢,或早或晚)都会发生变化。
2
在年老者和临终者(尤其是临终者)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情感方面,同样如此。受主题和时间限制,我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即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年老者与临终者屡见不鲜的隔绝。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说的,我关心的并非诊断年老者和临终者的生理症状——这些总是并非完全恰当地被描述为客观症状,而是诊断年老者和临终者自身的“主观”体验。我想为传统的医学诊断增添一种社会学的诊断,这种诊断聚焦于年老者和临终者被隔离后产生的危险。
在这个方面,人们可以发现在当下的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也即中世纪或早期工业社会)中,年老者和临终者的地位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前工业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口都居住在乡村,他们的生活仰赖于对土地的耕作,还有放牧,也就是说,农民和农场劳工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照看年老者和临终者是每个家庭的义务。当然,这种照顾可能是体贴温柔的,也可能是残暴冷酷的,但是这些社会中的年老者和临终者与发达社会中同样的群体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我可以列举两个差异。那些身体逐渐衰退的老年人一般会住在大家庭的生活空间范围之内,当然有时候和年轻的家庭成员之间也会有不小的纷争,但普遍来说他们基本都会死在家庭区域里。相应的,同城市化的工业社会相比,前工业社会中任何与衰老和死亡相关的事务都会更加公开,当然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传统。凡事都在大家庭内部(有的情况是在社区内部)变得更公开化,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年老者和临终者得到的都是体贴善意的照顾。毫无疑问,对年轻一代而言,在他们逐渐获得权力的过程中,非常恶劣甚至残酷地对待老年人,并非稀奇现象。但国家也不会费心插手这些事务。
今天,在发达社会中,国家像保护其他任何公民一样,保护年老者和临终者免于明显的身体暴力伤害。但与此同时,人们一旦开始变老变弱,就会和社会,和他们的家庭、熟人圈子越来越隔离。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出现,那些之前彼此并不相识的老年人居住在了一起。即使我们的社会是如此高度个体化,大多数人仍然在退休之前不仅和自己的家人,而且和或大或小的朋友熟人圈子建立了情感的纽带。衰老自身就会让最狭窄的家庭圈子之外那些情感纽带日渐萎缩。除了那些已经结婚多年的老年夫妻,住进一家养老院通常不仅意味着最终切断了过往所有的情感纽带,而且意味着个人将和那些并无积极情感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医生或护士所能提供的生理上的照料也许很好,但同时,老年人也被从正常的生活中隔离了出去,只能与陌生人聚集,对个体来说,这就意味着孤独。
我在这里并不仅仅关注他们的性需求(人在高龄时仍有非常强烈的性需求,尤其对男性群体而言),而且关注那些喜欢陪伴彼此的人(即那些彼此有特殊依恋的人)之间存在的那种情感效价(emotional valencies)。这种类型的关系同样会伴随老年人入住养老院而衰减,他们在其中也找不到替代物。很多养老院因此成了孤独的沙漠。
3
如果我们将晚近社会中处理死亡事宜的流程和面对死亡的普遍态度同欠发达社会相比较,我们就会清晰看到发达工业社会里临终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其中,情感隔离是最主要特征之一。所有人都很熟悉早期的那些画面,全体家庭成员(女人、男人和孩子们)都聚集在即将告别人世的女性家长或者男性家长的卧榻之前。这可能是一种浪漫的想象。那种境况中的家人事实上可能非常亵慢、粗鲁和冷漠。有钱人可能无法如他们的后代所期待的那样迅速死掉。穷人可能躺在自己的秽物里慢慢饿死。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甚至在19世纪之前,大多数人死去时,身边都有他人在场,只是因为人们还不像今天这样习惯独自生活。而且,并没有足够的房间可以允许一个人独自待着。早期社会里,临终者和死者并不像晚近社会中这样普遍地与公共生活严格隔离。这种早期社会在经济上也更为贫穷,他们也不像晚近社会这样拥有健全的卫生制度。欧洲大陆频繁被大瘟疫洗劫,从13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基本上每个世纪都要爆发几次大瘟疫,人们只有到20世纪才至少开始学习如何应对。
4
要后来人去想象先前人的生活并非易事,所以后来人其实也无法正确理解自身的处境,或者自己。真相就是,早期社会里关于死亡及其成因的知识储备,不仅非常有限,而且远远没有今天来得可靠。当人们缺乏对现实可靠的认知,他们自己也会暴露在更大的不安全感当中;他们更容易激动,也更容易恐慌;他们通过幻想的知识来弥补自己对现实认识的鸿沟;同样,他们也试图通过各种幻想的手段来缓和自己对无法解释的危险的恐惧。所以先前的人试图用护身符、祭献、控诉水井投毒者和女巫,甚至是自身的原罪,作为平定自身狂躁情绪的手段,以对抗周期性的瘟疫。
当然,那些患上不治之症或者因其他缘故走向死亡的人,会听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说这都是他们亲属的错,或是对他们自身罪过的惩罚。这种情况当下仍然存在。但今天,这些个人幻想不大可能被误认为真实的公共知识,人们通常会认识到它们是个人幻想。对疾病、衰老和死亡成因的认知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全面。符合现实的知识增长在改变人类感受与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对致命大瘟疫的控制仅仅是其中诸多例证之一。
5
通过幻想得出解释是颇令人激动的。将它的这种退出(或者用马克斯·韦伯相当情绪性的表述,这种“世界的祛魅”)看作一种理性化过程,也许多少会引起些误导。不管这个术语如何被使用,它都在暗示最后是人类的“理性”发生了变化;它似乎也在暗示,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日益趋于理性化,通俗点说,变得更加明智了。这种自我评价显然和事实相去甚远。我们只有意识到这其中蕴含的一种变化,即事实导向的社会知识(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知识)有所增长,我们才能开始理解诸如“理性化”这类概念所指代的变化。现实型知识不断扩张,幻想型知识相应不断萎缩,与此同步的是有效控制多种状况能力的增强。这些状况可以是于人有益的,也有可以是对人构成威胁和风险的。衰老和死亡就属于后者。如果我们尝试理解,在这些领域,更加现实导向的知识对人类的控制力有多么关键的影响,我们就会遇到奇怪的一幕。
在过去两百年里,社会上积累的关于衰老和死亡的生物学知识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这两个领域的知识本身变得根基日益稳固、更加符合现实。随着这种知识的增长,我们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大。但是在生物学层面上,当我们试图将人类对衰老和死亡的控制往更深处推进时,我们似乎就遭遇了一个完全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不时提醒我们,和自然宇宙的伟力比起来,人类所拥有的力量仍有一定限度。
生物学知识的进步使大幅度提高个体寿命预期变得可能。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不管是借助医疗和药物的进步,还是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延长个体寿命、降低衰老和死亡本身带来的痛苦,个体的死亡仍和其他诸多事件一样,揭示了人类日益强大地控制自然时仍面临的局限。毫无疑问,在很多领域,这类控制之广泛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驾驭自然事件时可以不受任何束缚。
就目前已知的来看,这样的结论并不适用于人类生活的社会层面。在这个领域,人类欲实现的目标目前看不到任何绝对的限制,而且遇到这种限制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但在扩张自己的知识和控制力时,人们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足以摧毁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倒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即使这些艰难险阻绝非不可跨越。人类行动的绝对障碍存在于宇宙的前人类阶段——我们称之为“自然”。但在使用“社会”和“个体”这种概念指称的人类–社会阶段,这些障碍仅存在于这样的情况,即上述阶段将不可教化的自然也包含在内,或者其本身内嵌于这种自然之内。
这些障碍目前正对“人类至上”和人们控制自身事务造成严重妨害,但绝不是不可逾越的。在此我要顺便提到其中的两个。第一是那种被普遍视为不证自明的价值的等级。“自然”,也即人类存在之前的非人为事件范畴,其中包含的价值远远高于人类自身构建和创造的“文化”或“社会”。“自然”的永恒秩序令人敬畏,且和人类社会的混乱、不稳定形成对照。很多人成年以后仍在在寻找一个接近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寻找可以牵起他们的手为他们指引方向的人。“自然”便是这些形象中的一个。人们假定自然的一切作为,以及任何“自然”的东西,对人类都是良善的、有益的。牛顿描述的那个和谐而规律的“自然”,可以在康德对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的崇拜中得到表达。但是牛顿描摹的“自然”的美丽画面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很轻易就忘记了,“自然”的概念如今等同于宇宙学家们认为属于宇宙演化的东西——无目的的膨胀扩张,不计其数的太阳和星系的诞生和灭亡,还有吞噬光的“黑洞”。不管我们是用“秩序”还是“偶然”抑或“混沌”来描述它,背后其实都是一回事。
同样,说自然事件对人类是有利或有害,并没有多少意义。“自然”是没有意向的,它并没有什么目标,完全是无目的的。浩渺宇宙,唯一能够树立目标、创造并赋予意义的,只有人类自身。但对很多人而言,决定何种目标是人类应当追求的,何种计划和行为对人类来说具有或没有意义,这样的重担落到自己肩上,他们仍然是无法想象。他们永远在寻找一个人,一个制定规则决定他们应当如何生活,决定什么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人,来替他们承担起这样的重负。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外部的、预定的意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自己,最终是人类全体,创造了一种能指引他们生活的意义。
人类的成长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学习期很长,严重的错误无法避免。在学习的过程中,自我毁灭和外部生存条件消亡的风险都是巨大的。但这种危险只会因为那些自视为婴儿的人类的存在而愈加严重,对于那些人而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别人为他们承担全部。认为自然(如果其拥有自主状态的话)会对人类及其公共生活做正确的决定,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它证明了,那些只有人类能做出的决定及其责任,是如何被推到一个想象的母亲的形象(“自然”)那里去的。但将这些托付给自然是吉凶未卜的。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无疑布满危险,但人类可以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非人类的自然进程则不具备思考的能力。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人类社会自身就是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和此前所有的阶段都截然不同,因为人类可以根据集体或个人的经验,也即学习过程来改变自身的行为和感受。人类这种适应性比其他生物都要来得广泛,而且独一无二。这种改变的能力对于人类而言应该是极为珍贵的。但人类对不朽的渴望同样也会将他们引入歧途,将他们引向那些不朽的象征,比如在他们想象里恒定不变、至高无上的“自然”,而不是让他们面对真实的自身,面对自己所处的集体生活,面对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其自身进行的控制的程度和模式的变化。也许,也许读到这里时,他们仍然会对这种探索所带来的必然的价值重估感到抵触。这是我所指的障碍之一。
第二个我想例举的障碍和人们在现阶段无法具备的认识相关。人们无法意识到,在他们自己与他人共同建构的现实范畴中,长期且非计划性但有其特定结构和方向的变化正在发生,而这些进程和无法控制的自然进程一样,正将他们不由自主地推向某个方向。由于他们无法认识类似这种非计划性的社会进程,因而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也没有合适的手段介入或者控制它们。能反映现今的人们无法认识这种非计划性进程的例子就是,他们一再被卷入战争。(在此我只能顺带一提,不同国家之间自由竞争的动态变迁,以及我在拙著《文明的进程》第二卷中讨论过的“垄断机制”是通向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国家已经高度文明化了,杀戮他人并不能给其内部成员带来特别的愉悦,而且其内部成员在战争中死去也不再是一件多么荣耀高尚的事。同理,今天的人们无助地面对战争的风险,和更早之前的人们无助地面对河道溃堤导致的无力纾解的洪灾,或是吞噬全国千万人口的大瘟疫一样,这中间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已经提到了通过诸如“自然”和“文化”这样的对立将外在于人类的自然和人类–社会进程的关系概念化,毫无疑问,人们为前者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要让20世纪晚期的人们相信,原初的“自然”并不很契合人类的需求,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清除了原始森林,将狼、野猫、毒蛇和蝎子(简而言之,所有会威胁到人类的事物)通通消灭,只有当“自然”被驯化,从根本上被人类改造,对那些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而言,这样的“自然”才是仁慈且美好的。事实上,自然有自己的进程,它盲目地不加区分地将好的和坏的,将健康的喜悦和疾病的痛苦赋予人类。唯一能在必要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无情的自然进程并互相扶持的生物,只有人类自身。
医生能完成这样的救治,或者他们至少尝试如此。但也许,即便是医生,也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被“自然进程才是病人康复的关键”这样的观念所影响。有时候,事实的确如此,有时则不然。僵硬的教条在这里于事无补,关键是要对自然的仁慈和恶意具有一种非教条的理解。在当下,医学知识经常仅仅被等同于生物学知识。但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有一天,关于人类的知识,关于人们之间关系的知识,关于他们之间的纽带并因之彼此加诸压力与限制的知识,同样也会是医学知识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属于这种知识的分支。有一种可能是,人们生活的社会面向,也即他们与他人之体间的关系,之所以对走向衰老和死亡的人来说特别重要,恰恰是因为盲目而不可控的自然进程很明显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但对医生、对年长者和临终者的亲友而言,一旦意识到已经抵达了对自然控制的极限,他们往往会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往往同年长者和临终者的社会需求是对立的。人们往往会告诉自己,他们能做的已经不多,他们会耸耸肩,不无遗憾地走自己的路。医生尤其如此,他们的职业就是要掌控自然盲目的毁灭力,却常常惊恐地、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盲目的力量是如何在病人和临终者身上打破有机体日常的自我平衡,势如破竹地摧毁有机体自身的。
当然,让人们镇定自若地见证这种衰朽过程并非易事。但也许处在这种境况中的人,对他人也会有一种特殊的需要。他们需要获得一些信号,能显示他们和他人的纽带没有切断,或者能说明虽然他们即将离开人世,但世间的人依然很重视他们。这些信号对他们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此刻变得非常虚弱,更像是过去的自己的一个影子。但对某些临终者而言,孑然一身面对死亡也许更好。也许他们依然能够做梦,希望自己不被打扰。人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他们需要的。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死亡变得更加随意、非正式,而个体的需求(如果它们为人所知的话)其实越来越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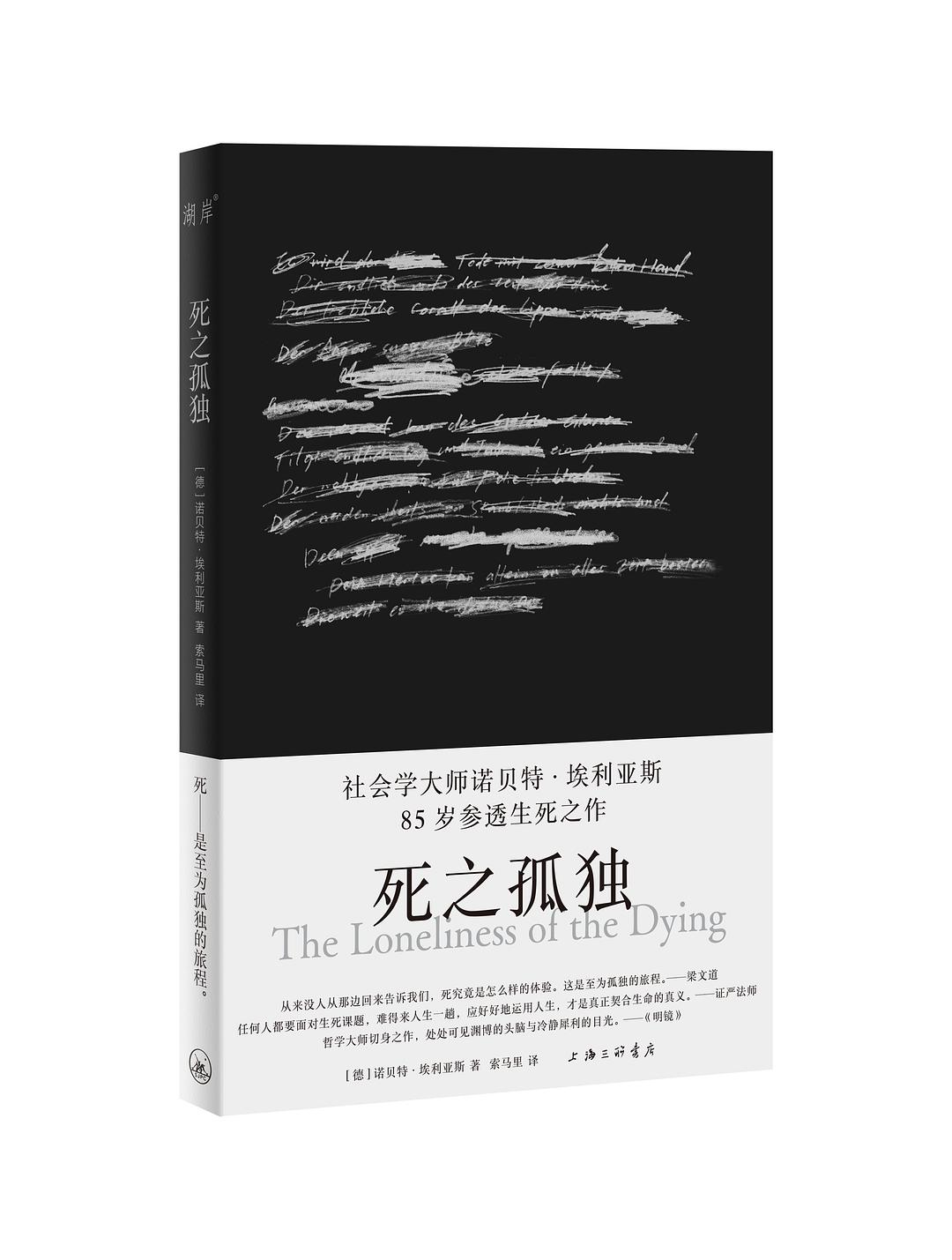
(本文选摘自《死之孤独》,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