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昨日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分享活动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起了他在很多场合跟人辩论的经历。他说,“很多理工科大学校长觉得‘五四’把事情搞砸了,如果不是‘五四’,今天五千年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甚至有些人故意将‘五四’和文革挂上。”
他联系新作《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表示,现在讨论“五四”的好处在于它是众声喧哗的,没有形成主调。怎么看传统、如何评估传统连续与断裂,以及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话题很具有挑战性。陈平原说,希望讨论“五四”可以不封闭于专业和学院,而是真正地进入社会和公共生活,因为“五四”跟当下中国文化的走向和思想脉络有关,也与年轻人的生活相连。

“我们(指在场三位嘉宾,分别是陈平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的思考已经固定下来了,没有像年轻人那么敏感。五四那代人比我们年轻多了。我的老师王瑶先生常常会算账,不要忘记‘五四’那年,蔡元培最大51岁,鲁迅38岁,胡适27岁——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是十多岁二十岁的人。”陈平原说,以往谈五四常常关注的是老师那一辈人,事实上真正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是学生。
俞平伯回忆道,在北京大学1917级国文系,“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他们办的杂志诸如《新潮》《国民》和《国故》都影响了之后的政策、思想和学说。在今天,“五四”还能与年轻一辈对话吗?陈平原发出了这样的提问。在法国,人们常常回顾大革命,在对话中确认它作为现代法国乃至现代世界的起点,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
只有理解那代人的处境,才能理解他们的努力和论述,五四文人与太平文人的表达不一样。陈平原指出,太平年代在书斋里做文章可以四平八稳,可是五四人身处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没有那么多的书生考量。“不要高估五四人的学养,也不要低估他们求知的热情。”五四学人考虑的确实就是拿来就用,他们的知识很多都是从媒体、报纸、杂志而不是教科书中来的,写作和表达也是迅速、直接、激烈和极端。陈平原由此也提醒今天的读者注意:今天阅读那代人的思考和表达,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那是危机时刻的表达,才能理解和接受其中的疏漏和偏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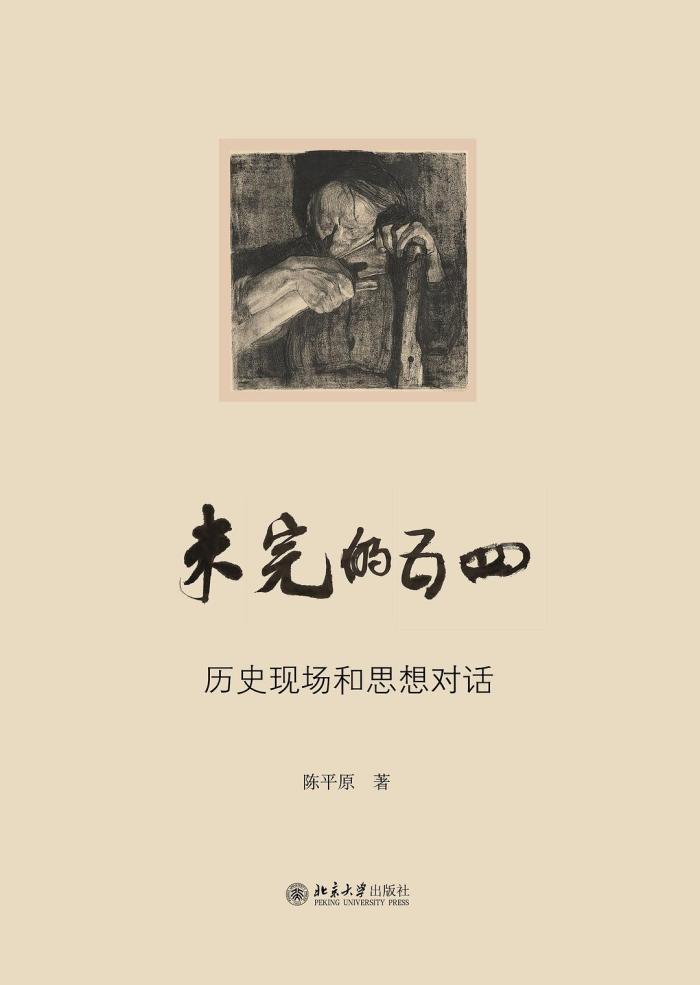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4
人们在了解和审视“五四”时,还应当注意到那些被置于新文化“对立面”的人物,比如辜鸿铭与林纾。“蔡元培先生在1919年说,不会因为辜鸿铭提倡帝制就不聘他,可是请注意,第二年辜鸿铭就被解聘了。”陈平原说,辜鸿铭的解聘是因为学生罗家伦告状:他上英文诗歌课上大部分时间都在骂新文化。
陈平原提到,林纾借助小说《荆生》发动军阀打压“五四”有讹传成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是碰到过困难,但始终没有摆在台面上的斗争。”他解释道,林纾之所以写这篇小说,跟他自身热爱武术、喜欢想象游侠生活又爱讲诙谐话有关,“赞成新文化的声音后来占了上风,可这不等于反对者就应当是被唾弃的。”
主流“五四”叙述之外遗忘的人物还包括“性学专家”张竞生。陈平原介绍,张竞生留学法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在1920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长达五年。1922年,美国计划生育创导者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应邀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讲演时,就由胡适和张竞生陪同。陈平原说,“当年张竞生的名望一点不比胡适低。他们一个是留美的,一个是留法的;一个强调杜威,一个学习卢梭。”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起爱情大讨论时得到过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众人的支持,出版《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时也得到过周作人的欣赏。但他后来的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1926年,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征求大学生的性经验,“希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之后集合了张竞生序言以及几篇自述的《性史》出版,惹出了不小的事端。“他被正人君子骂到狗血淋头,又有很多出版商紧急跟进(《性史》的出版),然而后来出版的几辑都不是他的,还有明清色情小说摘过来的出成集子。”自此,哲学博士就戴上了性学专家的帽子,他也离开了北大,从新文化的叙述中退场。
陈平原提示读者注意,打压他的恰恰不是守旧派,而是新文化人,因为人们担心他把一个本来有价值的东西给糟蹋了。现在学生看了张竞生的作品可能会说没什么,可这在一百年前就闯了大祸。对于这一部分历史的还原,可以让丰富人们对“五四”和新文化的认知,陈平原讲道,“为什么讲杜威的日后名满天下,学卢梭的后来举步维艰?这让我们了解新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哪些是可以努力的,还有哪些是陷阱。 ”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